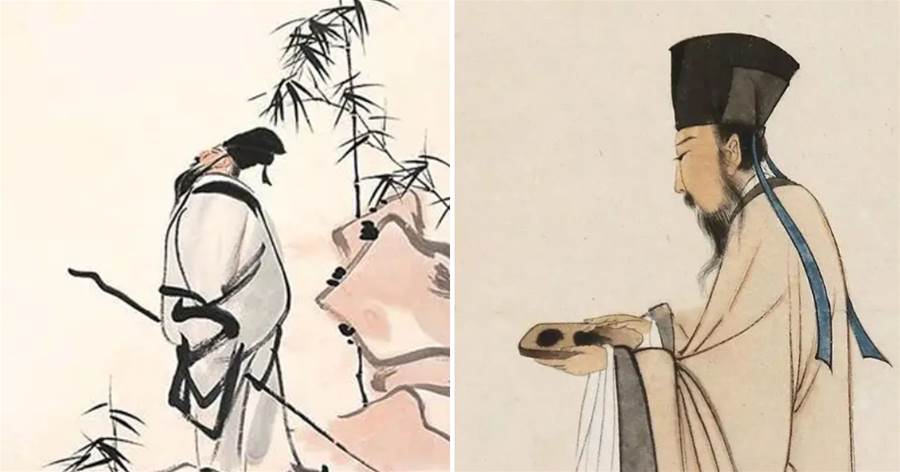
曾有讀者問過我,為什麼世人總是把蘇東坡的一生寫得凄凄慘慘,以他的家世和聲名而言,比起普通人不知要好上多少?
所以這位讀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:他也不過是犯了文人的通病,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罷了!

事實上,這位讀者的話并沒有什麼錯。
在眉州故里,蘇家是頗有恒產的,且聲望斐然,蘇東坡的祖母史家,是當地的望族,其父蘇洵雖早年不太著調,但娶得卻是眉山首富程文英之女,所以他才能得到時任益州知州(后升副宰相)張方平的欣賞,把他們爺仨一同推薦給了歐陽修。
歐陽修彼時早已名滿天下,且和梅堯臣同為京試的主考官。

就這樣三蘇父子一起上路,趕赴汴京參加科考,蘇東坡和蘇轍一起中第。
若不是歐陽修為了避嫌自己的門生曾鞏,蘇東坡便是那一年的狀元郎。
不久后,蘇母過世,蘇東坡還鄉守孝三年,再回京時參加制科考試,為百年第一,三年京察開始,簽鳳翔府判官。
三年期滿后,蘇東坡辭別學生董傳,寫下那兩句名垂青史的詩:粗繒大布裹生涯,腹有詩書氣自華。
就在蘇東坡欲大展拳腳的時候,他的愛妻王弗和家父蘇洵又相繼過世了,不得已,蘇東坡回家丁憂三年。

等蘇東坡再還朝時,王安石已經開始著手推動變法,朝局變換,今非昔比。
而且他和王安石政見不合,因上疏論述王安石變法的弊端,被王安石授意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談論他的過失。
無奈之下,蘇東坡自請出朝,去往杭州任通判。
自此以后,蘇東坡就開始了漫長的轉官和貶謫生涯,尤其是「烏台詩案」后差點丟了性命,因王安石為他求情,才貶去黃州4年,這一走就是到65歲終老,可謂是大半生都在顛沛流離。
但換個角度看,除了黃州團練副使4年,其余時間蘇東坡基本都是以知州身份在位任職(市長),期間還升翰林學士、知制誥,知禮部貢舉,及龍圖閣學士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下一頁


















